前沿拓展:百科全说女性服装与性格
以一个男主角为视点,表现纷纭众多的女性形象,不落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老套,一个个栩栩如生,妍媸互见,洋洋蔚为大观,以再现复杂的世相,寄托作者的情趣和情思,这是《金瓶梅》和《红楼梦》的共同特点,也是它为其他小说所难以望尘之处。
但如果从思想高度和审美品格上对二书所刻画的女性群象试加比较,你就会发现二者之间是那样的不同和出人意外的复杂:一方面她们善恶殊途,美丑判然;同时她们间又异中有同,殊途同归,无论从艺术欣赏和艺术创作的角度看,这都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课题。
美丑判然品格迥异就女性形象的群体而言,《金瓶梅》所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丑,《红楼梦》所给人的印象是美:二者品格迥异,美丑判然。
《红楼梦》既是女儿的悲剧,也是女儿的颂歌。
「山川日月之精华秀灵独钟于女儿」,「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不光是贾宝玉,红楼中的女儿,谁见了都会感到「清爽」;而《金瓶梅》恰好相反,那里的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是「泥做的骨肉」,是造物主所遗弃的「渣滓浊沫」,她使人感到「浊臭逼人」。
张竹坡云:「金瓶里有许多好人,却都是男人,并无一个好女人。」
他的话未免有些偏激,但若从是书在宏观上所给人的印象,把它作为和红楼女儿鲜明的对照而言,是论亦「庶几乎」矣。
贾宝玉的「芙蓉女儿诔」赞晴雯「其为质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貌花月不足喻其色」,他诔的是晴雯,也是黛玉,也是红楼中的众女儿。
《从金瓶梅到红楼梦》
雪芹笔下的女儿,作为悲剧形象的整体看,无论其追求和志趣,其性情和品格,其教养和才华,其容貌和风韵,她们都无愧于天地钟粹毓秀。
她们不仅是传统糟粕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古代文化精华的负载者,而且她们作为种种邪恶的对比观照,更是美好未来的体现者。
红楼女儿的美,可以概括为三点:曰文,曰真,曰情,让我们与金瓶中女性试加对照而言之。
大观园中女儿属于文化型和典雅型,金瓶中「诸妇人」属于市井型和庸俗型。
王熙凤是个名门出身的贵族少奶奶,贾母诩为懂得大礼,李纨犹骂她是「专会分斤掰两」的「泥腿光棍」,可见红楼女儿的文化眼界是如何之高了。
大观园是典范的东方沙龙,文采风流的众女儿是这里的主人,从结社吟诗,即兴联韵,因事题咏,酒宴行令,直到日常生活的言谈应对,她们的生活是文化化了的。
探寻一下她们精神生活的步履,几乎可以扫描出我国整个古典文化的图景。
这里经常进行的除了吟诗作赋外,还有宣讲哲理,顿悟禅锋,论画评书,品曲谈琴,鉴赏古玩,围棋射覆,烹饪品茗,举凡色织雕塑、园林建筑、医卜星相,无不异彩纷呈、琳琅满目。
女儿中的佼佼者,如宝钗、黛玉、湘云、妙玉自不待言,即使是薛大傻子用银子买来的「贱妾」香菱,也十分憧憬那女儿的乐园和文化的王国,一旦有幸进入其间,流风所被,苦吟学诗,也可写出颇有灵性的篇章。
这里的女儿,不唯式微如湘云不识当票子,精明如探春不知豆芽儿几文钱一斤,清贫如岫烟来去如闲云野鹤,即使怡红院的女奴们,也多不识银戥子,不以多给医生一二两马钱为意,即使是骂人,鸳鸯也可以信手拈来「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的典故,十分新雅。

87版电视剧《红楼梦》剧照
可是在西门大官人的后院,我们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市井文化似乎就是以直露的、粗俗的方式进行着物欲和肉欲的宣泄。
在这里,潘金莲堪作其代表。她虽然也「知书识字」,但那是出于学习弹唱的需要;她虽能品丝弹竹,但那属于乐伎行当,谈不上艺术和性灵;描眉画眼,傅粉施朱,做张做致,乔模乔样,是她的风韵;帘下嗑瓜子,帘外露金莲,满带金马蹬戒指,把瓜子皮吐在行人身上,是她的举止;
「我若饶了这奴才,除非他×出我来!」「我如今整日不教狗攮,却叫谁攮哩?」,是她的语言;鬼步潜踪,勃豀斗法,争风吃醋,撒拨放刁,分斤掰两,锱铢计较,打情骂俏,白昼宣淫,私仆引婿,肉欲横流,这是她的品行。
对于肉和物的不择手段的追求可以把人扭曲成什么样子,使人丑恶到什么程度,不妨看看潘金莲。
西门家的女奴们虽也穿绸着缎,插金戴银,可大率粗俗不堪。
大观园女儿斗草游戏,「呆香菱情解石榴裙」的场面,多么富于诗情画意啊!
可月娘房里的「二玉」挝子儿玩,小玉把玉萧骑在身下,却笑骂道:「贼淫妇,输瓜子,不教我打!」因叫「蕙莲嫂子,你过来,扯着淫妇一只腿,等我×这淫妇一下子!」淫风所被,连未婚少女的语言也如此不堪。
芳官和赵姨娘吵架,用的是很诙谐的歇后语:「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罢哩!」可蕙莲骂孙雪峨却是「我是奴才淫妇,你是奴才小妇,我养汉养主子,强如你养奴才!」固生动矣,美即未必。
张竹坡说金瓶写诸人,多用「俏笔」或「傲笔」,然全无「文笔」「秀笔」和「韵笔」。
是的,她们和红楼女儿相比,一文一野,一雅一俗,一美一丑,判然两种文化品格。
在这里,环境和人物的文化品格,作品的审美品格,与作者主体审美追求,应该说是一致的吧。
竹坡或谓「倘他当日发心不做此一篇市井文字,他必能另写出韵笔,作花娇月媚如《西厢》等文字也。」吾谓其未必为信然也。
《红楼梦》是古往今来第一部情书,宝玉是「圣之情者」。他之崇拜女儿,首先就因为她们「有情」。
黛玉、紫鹃、司棋、尤三姐等等,她们对所爱者之执着、缠绵、深沉、热烈、勇敢与忠贞,那一往无前的追求与崇高的奉献精神,自不必说,即使那些出场不多的女孩子,专一执着于贾蔷的龄官,扮演夫妻以假为真的藕官,不顾一切逃出寺院寻找情人的智能儿,她们都可称为「情痴」「情种」,她们的情怀使人感泣不已。
可在《金瓶梅》中我们只能看到欲的横流,看不见情的荡漾。
潘金莲一嫁再嫁,婚内婚外,外宠内遇,先后与张大户、武大郎、西门庆、琴书、陈敬济、王潮儿发生过性关系,从家主到小厮,从兄弟到女婿,兼收并蓄,细大不捐。
即使丈夫垂危,她也不放过;发卖途中他也要与媒婆之子「解渴」,她的「性饥渴」,足愧后人了。
如果说「有情」是人的一个基本标志,那么张竹坡说金莲「不是人」就不算过分了。
其余「诸淫妇」,也大同小异。噫,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
李瓶儿后期有些「痴情」,然他之所「痴」,乃是禽兽不如的流氓恶霸,看看她对蒋竹山的嘴脸吧:「我早知你这忘八砍了头是债桩,就瞎了眼也不嫁你,这中看不中吃的忘八!」
西门庆爱她「好个白□股儿」,她爱西门大官人「中看又中吃」─就是「医奴的药一般」。

戴敦邦绘 · 潘金莲
孟玉楼在作者笔下应该说是格调较高的人物了,她两次改嫁,来去匆匆,从容自如,讥以「扇坟之诮」固为不妥,但说亡者未亡两无情,总不算过分。
小说在结尾处出现个韩爱姐有些特别,她以母女同时卖淫始,以为一「风尘知己」守节终。
也许是作者自己也感到他笔下的无情世界过于丑恶过于沉闷了吧,故尔在匆匆收笔之际不无突兀地安排了这个表现人之情并未泯灭的故事,对浊臭逼人的色欲世界留下一声轻轻的叹息。
贾宝玉以一个「赤子」眼光去观照那由涉世未深的女儿们所组成的大观园世界,与那以男性为中心的虚假丑恶的污浊世界相对照,他发现了一种天真的美。
比起宝钗的圆通,颦儿全是一片纯真,她之吃亏在此,她之美也在此。晴雯撕扇,正是与宝玉一起演出的真与美的二重唱。
当贾母王夫人不在之际,每当查夜之后,怡红院的大门一关,女儿们恣意玩耍,这儿宛然成了一个游离于尘世之外洋溢着真与美的自由天地。
宝玉希望青春常驻,女儿不老,女孩子们也憧憬和留恋着这个自由王国。
春梅恃宠辱骂的是弱者孙雪娥和郁二姐,龄官所顶撞的却是贾府的「凤凰」宝二爷,不仅如此,「前日娘娘传我们进去,我还没有唱呢!」
即使芳官和莲花斗口齿,掰糕喂雀儿;莺儿编花篮,结络子,娇憨宛啭说宝钗,也都洋溢着天真的情趣。
可在金瓶世界中难得寻觅「无价珠宝」的闪光,所有的尽是些为尘世荼毒扭曲了的「死珠子」和「鱼眼睛」。
在那一世界里,无耻出卖色相,恣意宣泄肉欲,献媚邀宠,争风吃醋,噬啮同类,欺凌弱者,女人们脸上所呈现的不是凶相,即是媚相,归根结蒂是假相和无耻相。
清河的妓女们,既无云儿式的血泪,更无霍小玉、杜十娘般的痴情,她们几乎全是些没有心肝和廉耻的名副其实的「婊子」。
李桂姐一面千方百计向西门庆献媚邀宠任其玩弄,一面又教唆西门庆家丫头偷主子的东西,西门一死,马上给李娇儿传递、转移财物,大挖干爹的墙脚,随之就与干娘断绝了关系。
王六儿先私通小叔子,刮拉上西门大官人之后,笑脸马上变为棒槌,而且还唆使后来者把先前的情人捉进衙门,一夹二十,打得顺腿流血。
西门庆家的丫头,春梅恃宠欺侮雪娥和秋菊,而后者除了学舌头、搬是非、听壁脚、偷柑子等等,处处表现出一种贱相之外,看不出一点弱者的真情和骨气……这一假、丑、恶的女人世界,与真、善、美的女儿世界,形成强烈的对比观照。

戴敦邦绘 · 李桂姐
蒙昧觉醒对比鲜明神、政、族、夫四权,把中国妇女压在社会的底层,经过几千年的酿造,种种形而下的压迫力量又转化为形而上的观念,淤积于广大妇女的心灵深处,变成无形的枷锁,使她们甘居于奴性地位而不自觉,不欲自拔。
诚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呵!红楼中许多聪明清秀的女儿,诸如「金钗雪里埋」的宝钗,「枉与他人作笑谈」的李纨,禁于深宫「不得见人去处」的元春,「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探春,都是这样被毁灭的。
《红楼梦》之独步千古,还在于它成功地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厌弃奴性意识,带有不同程度觉醒色彩的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
「质本洁来还清去,强于污淖陷泥沟」的黛玉,「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宁折不弯的晴雯,以死抗争视荣国府大老爷为蔑如的鸳鸯,公然表明所爱毫不自愧自馁以死殉情的司棋和尤三姐,视侯府为牢坑率性本真渴望自由的十二个小戏子……她们在传统的女德之外,有某一方面的企求,作某一方面的抗争,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个性觉醒。
《金瓶梅》中女性则不然─尤其是其中的女奴,她们或逆来顺受,浑浑噩噩地安于现状,或以得到主子垂青而欣然自得,前者可以秋菊为代表,后者可以春梅为代表。
她俩同是潘金莲屋里的奴隶,可命运截然相反。潘金莲是一个奴性十足的婢妾,对凶兽显羊相,对羊显凶兽相。
在西门庆跟前,她什么下贱的事都干得出来;可在秋菊面前她又十分凶残,不仅主子架子十足,而且是个虐待狂。
可悲的是秋菊自己,主子踩了狗屎要拿她出气,丢了鞋要由春梅押着她去找,动不动就顶着大石头跪到天井里,拧脸蛋,挝耳刮子,扒了衣服打板子─连春梅都嫌打他污了手呢!
可她对这一切只会逆来顺受,除了「谷都着嘴」,只会「杀猪般地叫」,她至多感到有点委屈,不着边际地辩上两句,却从来未意识过这是多么地不合理。
她的自我意识与主子及高等奴隶对她的看法是一致的:贱。
后她也要报复了─绝不是奴隶的反抗,可却是通过给月娘打小报告的方式去实现,而且又做得那样愚蠢和窝囊,真使人感到压抑和悲哀!
比起红楼中那些闪光的女奴隶,秋菊给人的印象只能是:她不配有更好的命运!

戴敦邦绘 · 庞春梅
春梅和晴雯很有相似之处,同样「心比天高,身为下贱」,但晴雯之心高主要地不在于她的「风流灵巧」,而在于她的人格自我意识,正是这种意识使她与宝玉取得了感情的共鸣,而不是因为自己有可能成为宝二爷的屋里人而自傲。
而春梅正相反,以自己的姿色取得主子宠爱是她自傲的本钱,她以此傲视同类、作践弱者、唆打孙月娥、辱骂郁二姐,她「反认他乡是故乡」而不自觉,骨头里浸透了奴性意识。
秋菊不过是浑浑噩噩的奴隶,她则是万劫不复的奴才。
还有一类是被西门庆勾搭以出卖色相换取钱财的女性,如贲四嫂叶五儿、韩道国老婆王六儿、来旺妻宋蕙莲、来爵妻惠元、奶子如意儿等,在作者笔下,她们无不甘愿出卖肉体,以换取钱财为幸,以得到西门大官人宠爱为荣,一点看不出受侮辱受损害者的屈辱。
冯妈妈为西门庆拉纤时向王六儿说:「你若与他凹上了,愁没吃的,穿的,使的,用的!」
这些女性也真把这看作一场便宜买卖,每次交易总是一面心甘情愿地任其玩弄,一面总趁其欢心向西门庆讨点「好价钱」,要一对金头簪儿啦,一个乌金戒指儿啦,或一条妆花裙子、一匹蓝娟子啦,等等。
不错,《红楼梦》也有多姑娘、灯姑娘儿等等,但她们和「女儿」作对照只是少数,而且作者是把她们作为被侮辱损害者来写的,而在《金瓶梅》中她们则是多数,除了蕙莲后期有所觉醒之外,其余都处于蒙昧之中失去了被压迫者的「自我」。
金瓶中妓女更是充满了金粉气与市侩气,我们看到的只有趋炎附势、希宠市爱、打情骂俏与争风吃醋,很难见到辛酸与血泪。
善恶殊途相反相成十二钗的环境是文采风流的诗礼世家,《金瓶梅》的环境是庸俗不堪的市井社会:
一个是极富诗意的大观园,一个是人欲横流铜臭熏天的交易场;一个处于金字塔的顶部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一个躁动于社会的下层日益以自己的粗俗亵渎着古老的文明。
从文化形态看它们是对立的两极,可谁能想到那古老社会的庞大机体正是从这两极而不是从它那受压力重的底部断开了裂纹呢。

绘画 · 大观园
大观园的女儿和《金瓶梅》的妇人分别从两极出发各自以自己的方式破坏着传统的礼教精神:一则以情,一则以欲。
表现得为突出的是婚姻观念和贞操观念的变化。
传统礼教的残酷性在女性的道德要求上表现得为典型。「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把女性永远置于从属的地位,「德、容、言、工」「无才便是德」为女性的奴隶化制订了具体的规范。
宋明以后理学大师们更把「三从」升华为「一从」:「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把这种残酷性发展到了。
可是物极必反,也正是这时,我们也开始听到一些先进者为妇女解放所发出的呼喊,并看到了女德规范在事实上的改变。
在山东省清河县那发达的商业社会小环境中,在西门大官人周围,「从一而终」的传统美德对市井小民已经开始失去了魅力,「三从」公然被篡改成「先嫁由亲,后嫁由身」;男女苟合已司空见惯,平常自然,人们对此从不大惊小怪。清河县的真假神仙给妇女们看相或占卜,夫官克过几个方好,已成了一个基本话题。
西门大官人的如夫人队伍,就是由从良娼妓与再醮寡妇组成的,而西门一死,她们又「飞鸟各投林」─找新出路去了。
孟玉楼明公正地道嫁过三次,第一次书里未写,后两次都是由她自己亲自选择丈夫带着自己的财产嫁过去,后来还成了县尊衙内的令正。
贲四的娘子,韩道国的夫人,来旺媳妇,这些「小家碧玉」们大都来路不正而且婚后行为不端,她们与别人勾搭以出卖色相换取实惠,市井社会也反映平淡。
王六儿私通西门庆以致富甚至还得到丈夫的支持。一次西门庆在六儿跟前谈及此事,六儿说:「就是俺家那忘八来家,我也不和他。
想他恁在外做买卖,有钱,他不会养老婆的!」─公然标榜男盗女娼,还是性解放的先锋人物呢!
在诗礼传家的贾府,礼教的统治比市井社会严酷得多。封建家长们自不必说,追求自由婚姻挚爱着宝玉的黛玉,一旦面当情人借「妙词戏语」表白心曲时,马上翻脸不答应了─男女大防,婚姻他主的观念,已经转化为人们的下意识!
可是也就在这里,发生了令人惊心动魄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女儿大悲剧。
这悲剧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尊奉礼教规范的女德而成为牺牲者,如宝钗、元春、迎春然;一类是因抗争而牺牲者,如黛玉、晴雯、司棋然。群芳同碎,震撼人心。
《红楼梦》写的是悲剧,《金瓶梅》写的是喜剧。红楼女儿所殉的是情,金瓶妇人所追逐的是欲。
宝玉心目中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聪明清俊」「比天始天尊和阿弥陀佛还尊贵无对」呢,黛玉和晴雯是她们的出色代表。
她们为情而生,为情而死。而西门庆眼下的妇人,不过是供他玩弄的工具;他周围的女性也都是从这个前提出发去实现自己。
潘金莲是个性变态狂,李瓶儿先后抛弃花子虚和蒋竹山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他们满足不了自己的性要求,从林招宣夫人到王六儿、叶五儿,她们之欣赏西门庆,除了财势,便是其「好风月」。
「潘、驴、邓、小、闲」,正是金瓶中诸妇人的「葬花吟」和「秋窗赋」。
红楼女儿是以爱情为基础的自主婚姻与传统礼教相对抗,金瓶妇人是以自然欲望的释放在事实上破坏着传统观念。
红楼女儿虽反对封建婚姻但却忠于爱情,「从一而终」,之死靡它,宁愿为爱情作出牺牲;金瓶妇女以物欲肉欲为动力,通过「弃旧从新」及婚外性行为实现性解放。
一则以情,一则以欲;一则是美与善,一面是丑与恶,相反而相成,演出了破坏传统礼教的二重唱。
情天孽海清浊同归在《金瓶梅》的世界中,如果说刺激女性破坏传统伦理的是肉欲,那么推动他们建立新价值观念的则是物欲。
在商业社会的小气候环境中,这物欲又集中地表现为对于金钱的追逐和崇拜。
围绕着西门大官人转的有四种类型的女性:他的妻妾,女性奴婢,行院娼妓,市井妇人。西门庆的择妇标准,在传统的「四德」之外,又增加了一个「财」字,在姿容与钱财之间,他似乎更看重后者。

戴敦邦绘 · 孟玉楼
他在与金莲的热恋中忽然迷上了孟玉楼,而且几乎把前者忘却,就因为玉楼是富孀,很有钱。
瓶儿死后,西门庆痛不欲生,不无真情,而心腹小厮犹说他「为甚俺爹心疼?不是疼人,是疼钱」呢。西门庆的如夫人间穷富差别很大。
李瓶儿富,不仅潘金莲对她嫉妒得眼睛发红,连吴月娘都滴溜溜的大睁着眼睛盯着她的私房。
瓶儿死后,金莲通过讨好丈夫获得了她的一件价值六十两银子的皮袄,这件事使月娘耿耿于怀,成为一场家庭风波的动因之一。
孙雪娥穷,几房妾凑分子请西门庆和吴月娘,别人都拿现钱,她只好拔一根簪子以折价。
争头面,要衣裙,收受物事,拒发轿钱,乃至克扣奴才,偷盗元宝等等,在家庭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分斤掰两的斤斤计较。
这里的女性都精于计算,有很强的金钱观念,绝无湘云、麝月式的不识当票子与银戥子型的清雅女性。家庭生活中况且如此,余三者自不必说了。
李娇儿、吴银儿、郑爱月儿们出卖色相,是高度商业化了的;即使叶五、王六儿们之勾搭西门庆,也带有很强的商业色彩。
他们间之苟合往往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或一、二两散碎银子,或一匹娟子,或一、二件头面,基本上是当场兑现。
王六儿的「情郎」西门庆死后,韩道国欲拐走银子而于心有所不安,六儿却说:「自古有天理到没饭吃哩!他占用着老娘,使他这几两银子不差甚么!」
在那个世界里,一切是「有钱便流,无钱不流」,女人和男人们一样,「金钱是个好东西,谁见了都要眼睛发亮」,不同的是她们要通过向男人争媚献宠或出卖色相去获得,藉以实现自己的价值。
《金瓶梅》中女性的价值观念,以自我追求的格调而论,孟玉楼是她们的高代表。
这位布商遗孀,先嫁西门庆,后嫁李衙内,自己相亲,自己拍板,自带财产,不做举人老爷的正头娘子,甘为年轻富商之小妾。
她先后所嫁的对象都有钱,且懂得风月,其幸福标准中有较新的内容。
她像薛宝钗一样会做人和利用财物,但她的头脑里绝没有宝钗那么多的封建观念,可以说,她是市井上层人物理想的贤妻良母。
与金瓶的女性不同,红楼女儿们的自我追求带有浓厚的形而上色彩。
黛玉和晴雯是她们的好代表。她们的人生追求是通过爱情追求表现出来的。
不是夫荣妻贵,不是郎才女貌,「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她们所追求的是「知音」。「行为偏僻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她们与宝玉有着同调。
什么「经邦济世」「光宗耀祖」「修齐治平」,传统的人生价值观念中向来被视为神圣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失去了光彩。
她们追求的是什么?「我是为了我的心」!这是朦胧的自我意识,是对被种种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天理」所扼杀了的人性的呼唤。

87版《红楼梦》剧照 · 林黛玉(陈晓旭扮演)
人不应该是「禄蠹」,不应该是「泥猪癞狗」,不应该做物与心的奴隶,应该自然、本真、有自己的尊严和自由,应该还天地灵淑之气所钟的本来面目。
她们憧憬着一种新的人生,于是,追求这人生的人就成了其理想的寄托。
那的知音便成为其生命的全部:追求,归宿,自我印证,等等,她们为之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泪水。
通过他人表现自己,以空灵寄托实在,通过自我实现的方式去实现人生追求,「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泥沟」,这种追求以善与美的悲剧形式,与《金瓶梅》中妇女的物欲和肉欲的追求,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太虚幻境」正殿的宫门上有一个匾额,上面写着四个大字曰「孽海情天」,这是雪芹的「假语村言」。
如果在本来意义上使用这四个字,那么作为一组反义词它们正好是「金瓶」和「红楼」两个世界的好概括。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女性们,他们的追求尽管清浊不同,可是形成了两股洪流,同样冲刷着古老传统的堤坝。
《金瓶梅》和《红楼梦》塑造女性形象的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在划时代的意义上为我国古代小说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其中有几点特别值得重视:
放艺术观念,才能打破传统窠臼,一反才子佳人小说的老套,创造出如许斑驳陆离、璀璨夺目的女性群象,一个个个性鲜明、栩栩如生、性格丰满而又意蕴丰厚。
书在不同程度上从市民角度去看取生活,观照女性,才能通过艺术烛照出生活中发生的历史性变化的因素,或亵渎传统,或呼唤未来。
调不同,二书的艺术果亦迥异。
《红楼梦》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女儿悲剧,《金瓶梅》是一部肉欲横流的女性的喜剧。
撇开创作主体的传统局限,单就其新的因素而言,《金瓶梅》反映的是市民们对现实生活的自发情趣,而《红楼梦》所表现的是新兴社会力量对生活的历史性思考。
儿的赞美诗,《金瓶梅》却是一幅使人感到窒息的女人的百丑图:格调迥异,美丑判然。
这点也是本文所重点探讨的。它告诉我们,文学一定要美,要能给人以美的陶冶;迎合某一时期的庸俗时尚,以哗众取宠为自得,创造不出真正的艺术精品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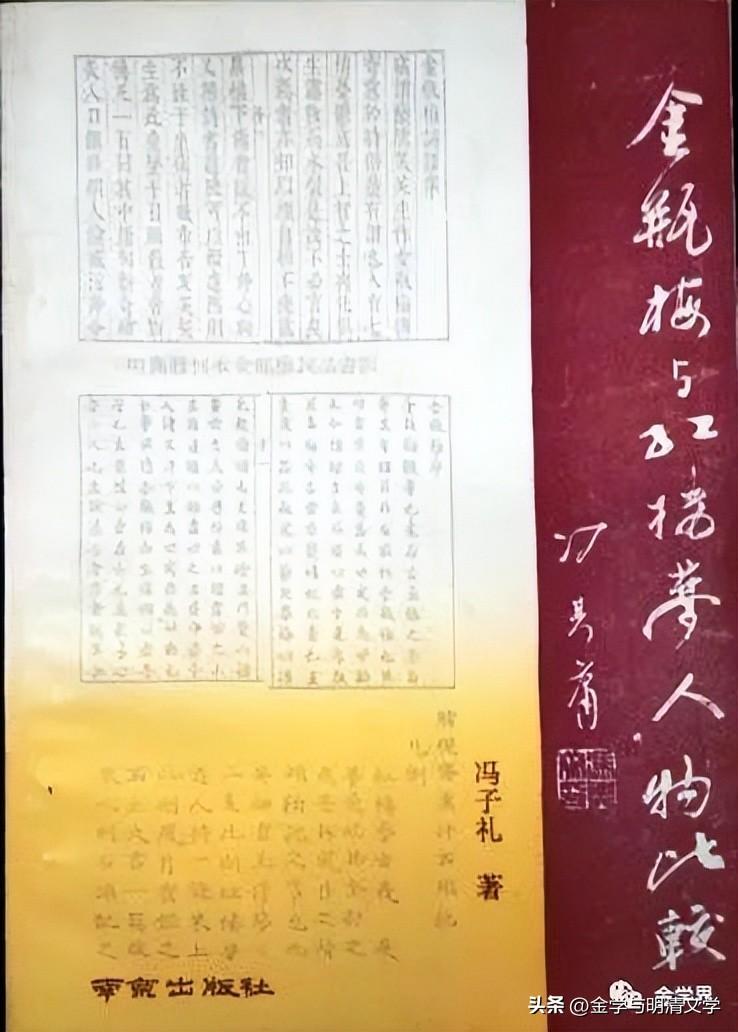
《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比较》 冯子礼 著
文章作者单位:江苏省运河高等师范学校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冯子礼<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拓展知识:百科全说女性服装与性格